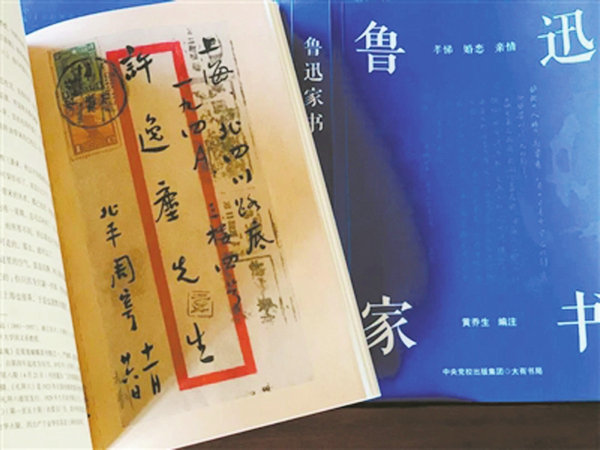□ 蒲晓蓉(绵阳)
我从小就比较安静,别家小孩子上湾跑下湾,满村子乱窜,而我却喜欢呆在家里,看哥哥姐姐读书,看父亲绘画写毛笔字。父亲见我不爱和小朋友打堆玩闹,便给了我几本小人书,让我自己翻着玩。虽然不识字,我还是翻得津津有味,那些穿盔甲骑大马拎长矛的武士,那些着红装施粉黛插凤钗的女子,在一幅幅生动的插图里或横刀立马,或顾盼生姿,咂摸着图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我逐渐品出了一个个英雄悲歌、倩女遗恨的故事。后来才知道,这些故事便是人人推崇的四大名著之水浒、三国和红楼什么的,父亲用几本连环画,算是给我启了四大名著的蒙。
我喜欢阅读,读书时代,经常一个人沉浸在书海里不能自拔,经常是任课老师进了教室,我还舍不得掩上书本,总是藏在抽屉里偷偷读完某一章节。遇到回家,我自恃小身子骨单薄,自告奋勇地争当了家里的火夫,于是,在哥哥姐姐弟弟们砍柴挑水打猪草清扫庭院时,我却可以坐在灶前趁一把火的空闲一目十行,惬意地享受着来之不易的阅读时光。
有一年,大姐已经工作,离家到一个很偏远的小学校驻点教书,为了晚上住宿安全,便带上我这个小妹到支点的学校读书作陪,我们回不了家,自然少了许多琐碎的家务,我则一个人坐在宿舍的木门槛上翻看连环画或者小说,从午后三四点经常读到夕阳西下,余晖照着黄色土墙、褐色木门和小小的我,自然构成一幅氛围静谧的油画。
那时候读物匮乏,我所能接触的基本是成年人的作品,诸如《红岩》《第二次握手》《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读得囫囵吞枣,似懂非懂,却又如饥似渴难以搁置,记得一本《青春之歌》破破烂烂前无开头后无结尾,我却反反复复翻看了三遍。
到了五年级,我回到了离家近的石龙小学就读,遇到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李鹏。如果说以前我的阅读出于个人兴趣,是一种自发行为,那么这位年轻书生则是我们进入文学殿堂的引领者。李老师不知从哪儿给我们借来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安徒生童话》等阅读刊物,让我们在课外时间自由阅读,甚至每周还专门留出一两节课作为阅读课,讲评书似地亲自为我们演绎文学作品。记忆最深的是他为我们讲《敌后武工队》,绘声绘色,引人入胜,英雄人物被他塑造得活灵活现,许多男孩子在课下游戏时争相模仿,以至于成年后这部红色经典还深深的根植在我们的脑海里。
到了初高中,学业开始紧张起来,课外阅读时间大大减少。我阅读的全部热情投放到课内仅有的几篇文学作品上,认真地听老师们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解读,饶有兴味地听他们进行咀嚼和延伸,难忘初中语文老师贾元正演绎的杨二嫂(鲁迅《故乡》中的人物),高中蒋武聪老师诵读的经典诗词《沁园春·雪》,两位老师其时皆五十岁左右,然而,男老师反串杨二嫂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尖酸刻薄,女老师诵读毛主席诗词时所展现的奔放和豪迈让我明白了文学作品实在是魅力无穷,它可以陶冶甚至改变一个人性情,让人达到忘我的境界。
当梦想照进现实,我们依然要阅读,后来读大学,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中文系。除了文学概论和中国的古代、现当代文学,也开始接触外国文学作品,小时候看过的不过是几篇情节简单的童话,真正捧上了诸如《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复活》等大部头巨著,才发现世界如此广阔,历史很宏远,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人类对命运的思考以及对时代的忧虑却始终是相通的。
岁月如梭,物质生活逐渐丰裕,信息网络飞速发展,读物不再匮乏,手上也有了大量可支配的阅读时间,然而阅读行为却越来越稀疏。这时候方才深刻领悟了随园主人“书非借而不能读”的正真含义,人的惰性真的很可怕,枕边放一本书,大多时候成了摆设,偶尔朋友推荐一部作品,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拖拖拉拉要读一两个月。读的时候偶尔跳出一些自以为深刻的感悟,却在下来的时候被手机里的八卦新闻和抖音小视频等驱赶得一干二净,所以一本书好不容易读完了,却没能及时的留下一星半点阅读感悟,感觉书最终是白读了。
人生漫漫,回想前几十年的生活,风风雨雨,到底还是阅读能让人安静,能让人内心喜悦,满足踏实。风平浪静的时候,呆在书中,岁月静好。遇事的时候,也拿起笔涂涂写写,把心事倾倒在纸上,悲喜便找到了安放的地方,用不着去叨扰身边任何一个人。这个时候,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阅读体验化成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落在纸上,便成了可抵御外侵的铠甲和铜墙铁壁,以及疲累时最可依靠的臂膀和港湾。
编辑: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