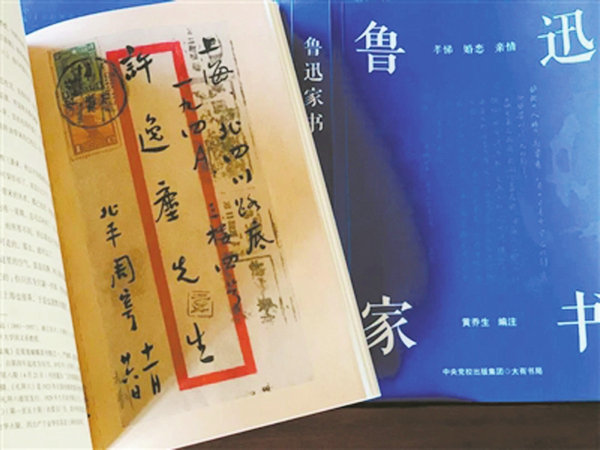◎廖伦涛(绵阳)
突然接到一位陌生男人的电话,那边传来有点淳厚沙哑的声音,他说他叫赵胜,过去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我的脑子迅速翻转着,终于记起来了。赵胜和我是盐亭北街的老邻居,长得高高瘦瘦、黑不溜秋的,我们1971年还一起下乡当过“知青”,由于他出身好,没两年就被部队招兵走了。后来,我们就再没见过面。
“疫情”中突然有了赵胜的音讯,我当然太激动,顾不上再说什么椒盐普通话,直接就用土得掉渣的盐亭腔大嚷起来:“你这个家伙,这些年啷跟(怎么)联系不上你?你都钻那卡卡角角(地方)去了?”赵胜也非常兴奋,他立刻改用浓浓的乡音告诉我,他身体还可以,在新疆当兵入党提干后和建设兵团一个女子结了婚,生活还不错,几十年来,就像一簇大漠边关的红柳在冰天雪地扎了根。连续几次通话后,他还说,只要一听到乡音和家乡的消息,就感觉到家乡并不遥远,这些天饭多吃了,话多了,觉也睡香了……
实在想不到分别50年,转眼青丝已白头,而远在千里之外的赵胜竟还能说出一口流利的家乡话。我的心里直嘀咕,一个人倍感亲切的是乡土,最不能忘亦是乡音啊。
前些年,“烟花三月下扬州”,我到江南走了趟亲戚。走在繁华的大街上,满耳都是吴侬软语,丝丝竹竹,甜甜绵绵,美如昆曲。江南经济发达,文风炽盛,气候宜人,风景秀丽,人的心性也十分淡定平和,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文文雅雅,语速平缓,声音较低。开始几天我也生怕我的粗喉咙大嗓门吓跑人,也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连我自己都想发笑的普通话。那日,饭做好了,一看没有酱油,慌忙去楼下一家商场,边递上塑料壶边说:“服务员,打斤酱油。”等到人家把酱油壶递给我时,我不由得惊呼道:“大妹子,这是哪哈(儿)的酱油?”话毕,女售货员先是一愣,尔后笑了。她问我:你是四川盐亭人?我也一惊:你咋个晓得?女服务员说,听你口音啊。她说她在扬州打工多年了,买了房子,结了婚,有个女儿,和我还是老乡。
其实,我调绵阳工作都30年了,早把他乡当故乡,可有时仍要冒点“盐亭腔”。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和她说了好一阵,还越说越近,原来她和我的亲戚同住在一个小区。以后,我们见面总爱笑一笑,打个招呼。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40多年来,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一向以“吃苦耐劳、读书发愤、老实忠厚、好胜逞强、死要面子”的盐亭人,不少在外的还是“混”(过)得有板有眼:有在成都开文化传播公司的,有在上海搞建筑的,有在深圳开广告公司的,有在广州开大酒楼的……当然,也少不了读书和搞科研教学的。总之,只要走到哪,兴许都能碰上几个老乡。一听口音,便知道是那方水土的。前几年我去“新马泰”旅游,在一公园的长凳刚坐下,一听两三个“老妞”的声音很特别也很熟悉,原来是盐亭金孔的。
《幼学诗》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首诗竟将“他乡遇故知”说成为四喜之一。如按此讲,这些年靠勤劳致富改变家乡面貌和家庭个人命运的,不知道有多少个“喜”呢!
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漫漫人生中,究竟是什么最能触碰我们心灵深处的柔软?应该是乡情乡音吧。乡音连着乡情,乡情系着国运。无论你在何方,无论你离开家乡的时间有多长,无论你如何的平常或风光,那个曾经“教你学吃饭、教你学走路、教你爱国家、教你听党话”的乡音,都是流淌在每个人心中的血液,拨动心底的琴弦,牵扯着生命和灵魂。
乡音,您真的最美!
编辑: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