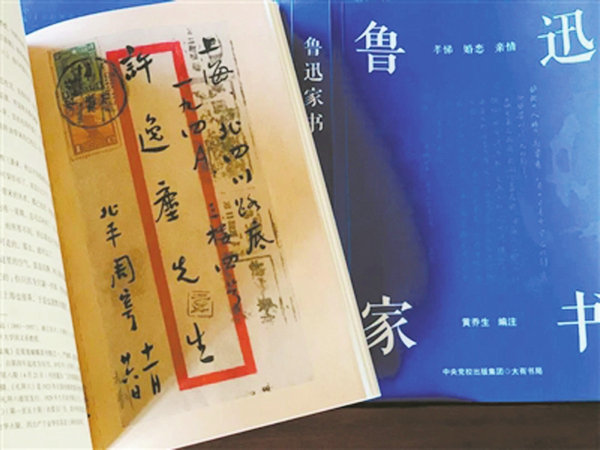□ 杨正钰(游仙)
“汤饼一杯银线乱,蒌蒿如箸玉簪横。”正如苏轼的诗词描述那样,面条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最喜欢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家常主食。我的父亲,就是一位做面条的乡村师傅。
我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到秋冬时节,村里人就挑一担小麦来到父亲的加工房,做一箩筐白花花的挂面,晚上煮一碗猪油葱花面,香气扑鼻,驱寒保暖。晚上吃少汤的面条最大好处是半夜不用顶着寒风去上厕所,可以一觉睡到天亮。
父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兵退伍回乡,就在本地农机站加工坊当会计,还负责加工面条。
相比打米磨面,加工面条的工序是最复杂的,首先要把一筐麦子用机器打碾成雪白的面粉,然后用水将面粉搅拌成面团,面团又通过机器模具压成一张长长的面皮,面皮再经过下一道模具压制成一排排细长的面条。机器压制出来的面条是湿的,要把一排排湿面条以2 米长为一段,对折对等地挂在一根根几十厘米长的竹棍上,架在露天坝子里接受太阳的暴晒,三四个小时后才能变成干面条。晒干的长面条切成约30 厘米的短面条,再用旧书旧报将面条一小捆一小捆地包裹起来。这样,从麦子到面条的制作工序就全部完成了。
面条可以根据需要加工成不同的宽度,有细如丝状的、有韭菜叶子宽的,也还有做到2 厘米宽的。因为不同宽度的面条有着不同的口感,所以乡亲们一箩筐麦子一般会做成几种不同宽度的面条。
据说是父亲做面的技术拿捏得最好。如,不同麦子去皮的次数、面粉和水的湿度、湿面条晾晒的时长、刀切干面条的力度等都要恰到好处,才能保证一筐麦子的出面率达到最高,而且面条煮在锅里不粘不连、不糊汤,吃起来不粗糙、有嚼劲、口感好。村里很多人还把父亲做的面条当作礼物,走亲戚的时候带上一两把。
时光荏苒,大量自动化生产的面条不断上市,冲击着农村面条加工市场。村里的两家面条加工坊早早关闭,可父亲还坚守着。吃过超市买的面条,村里人还是觉得父亲做的面条有麦子的味道、有太阳的味道,于是加工坊里又经常是十多筐麦子排起了长队……
加工面条是个体力活,打面、和面扬起的面灰很大,不到半天时间,父亲的全身都扑满了白花花的面粉,就连头发和眉毛都变白了。前几年,60多岁的父亲便不再加工面条了,可村里人经常找我父亲说,太阳晒干的面条好吃,有阳光的味道!想找他再加工些面条。听到乡邻的认可,父亲脸上总会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但只能抱歉地说,自己年纪大了,做不动面条了。
华夏从来多匠人,情怀悠悠默无闻。我发现,像父亲这样,一辈子坚守农村、技术过硬的篾匠、木匠、泥瓦匠、打米匠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通手艺人,一直会受到乡邻的尊重。也许,这些老匠人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工匠精神,承载着那个时代追求幸福生活的特别记忆吧。
砧上流金熔岁月,水中淬火注精神。当下,一些传统手艺正在慢慢消失,一些新行业和新技艺也正在兴起。一批批传承过去、继往开来的新生代民间工匠们,正在乡亲们最需要的地方,默默耕耘、辛勤付出着,将会慢慢成长为新时代最美好的乡村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