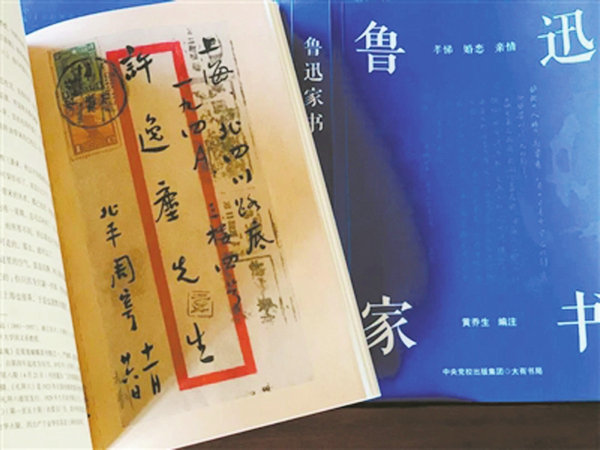古洋(绵阳)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家长辈里就出过两个“状元”,一个是我爷爷,一个是我父亲,都是放羊这一行的。
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之所以一直这么强调和宣传,是因为事实上人们是把职业分了高低贵贱的。农村里的农民,虽然都是农民,但因种地以外兼任的其他工种不同,也就有了高低贵贱。各个等级里,手艺人排名靠前,牧羊人排倒数第二,仅高于要饭为生的乞丐。再后来,农村人生活变好了,村里出去要饭的人逐渐没有了,牧羊人便是倒数第一。
牧羊人地位低,主要是因为这个活儿太苦了。每天太阳刚升起,就得把村里各家的羊集合在一起,一个人赶着羊群离开村子,到几里外的山坡上、草地里放牧。晚上太阳落山时,再把羊群赶回来,等上百只羊化整为零又各自回家归圈时,才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单纯种地的人,有农忙和农闲时,而牧羊人则没有闲暇。无论酷夏严冬,除了暴雨暴雪等少数极端天气外,一年365天包括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都得出工,更别指望周末和带薪休假了。风吹日晒雨淋是家常便饭,早些年还得防着狼。
更让牧羊人难熬的,是日日在旷野里一个人独自面对着一群羊的孤单和寂寞。电影《少林寺》中牧羊美女白无瑕“日出嵩山坳,林中惊飞鸟”式的悠悠和浪漫,也只有电影里才有。至于工资待遇,大集体时是挣一些不多的工分,包产到户后是每家按羊的数量交几块钱,都仅够在家里其他人种地之外再增加些微薄的贴补。所以每个村子,往往只有家里很穷的人才去当牧羊人,每个家庭教育孩子时,往往都会说一句,你若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去放羊。爷爷和父亲正好都家里很穷,又没有文化和种地之外的其他手艺,就只能当牧羊人,才能养活一家老小。他们在这个岗位上,先后都干过十几年。因为长年牧羊的日子里难得与人交流,所以性格都沉默寡言。后来,我每次在KTV点唱《北国之春》,到“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这句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俩。
虽然牧羊人卑微,甚至有些被人看不起,但我从小就未因为长辈们这个职业而有过半点自卑。他们不偷不抢,堂堂正正靠苦力吃饭,养活一家人,和所有辛劳勤勉的人一样,都值得尊敬。而且,作为牧羊人的孩子,耳濡目染,我比别人更清楚,放羊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能让一群不会说话的乌合之众服服帖帖,并非是个人就能做到的。一个团长、师长,你能指挥千军万马,并不见得能指挥几百只羊。小时候,我偶尔会提个挑野菜的筐子陪伴爷爷或父亲放羊,经常看到他们一声吆喝、一个挥鞭,就可以让企图溜进田地里吃庄稼的羊乖乖扭头,可以让跑远离群的羊迅速归队。我自己也试过,但任凭我如何去吆喝追赶,都起不到同样的效果。有时,遇到“不讲武德”、专门欺负小孩的长着大粗角的公羊,不但不听话,还作势要用头来撞你。
有一次,父亲和邻村另外一个牧羊人一处放牧,两个人坐着聊天,两群羊很快就混杂到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无法分辨,他俩却完全不担心。等到要回家时,两人分别站开,各自喊几声,甩几下长长的牧羊鞭,羊群便很快分离,各自集合,没有一只站错队,这让我感到很神奇。父亲告诉我,羊是通人性的,放羊也有很多门道,比如要让羊学会听口令,还比如要发挥好头羊的作用,等等。这简直和那些管理团队的CEO们没有两样。显然,在管理属于他们自己的“团队”方面,爷爷和父亲都是专业的,如果牧羊人也有段位的话,我认为,他们都应该是九段。甚至,即使我后来在部队当政委时,从管理效果上看,也不见得比他们做得更好。
牧羊人风里来雨里去,很苦。但也有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山里有很多的野葱、野韭、野蔬、野果,整天放牧的人便有更多的机会采摘。我和弟弟也就比村里其他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吃到这些美味。有时,父亲还会逮回来一两只黄鼠,这种比老鼠大得多、全身红黄的动物,在故乡号称是与天鹅肉并列的四大美味之一。天鹅肉没有吃过,而黄鼠裹上调料烤熟后,味道非常难忘,完胜现在的各式烤肉。
每年雨季,草地上还会长出很多白厚鲜肥的各类野蘑菇,形成大片大片的“蘑菇盘”,年年在同一处复生。牧羊人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清楚哪里有蘑菇,哪种蘑菇有毒无毒。每年夏秋时节,父亲总是能摘回一口袋一口袋的蘑菇。吃故乡的特色食品莜面时,配上碗蘑菇汤,堪称人间佳肴。母亲经常把吃不完的鲜蘑菇晒干,送给亲戚朋友。也许他们只有在吃这些蘑菇的时候,才会忽然觉得,平时认为没什么出息的放羊人穷亲戚,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1990年我考上四川大学,父亲高兴坏了。他在家里请了一桌客,客人齐刷刷地都是各个邻村的牧羊人——父亲的“牧友”们。由清一色羊倌参加的另类升学宴,后来作为一个几丝酸涩的故事,在乡邻中广为流传。一个牧羊人子弟的升学庆典,都由牧羊人来参加,岂不正好是情理之中?
我上大学了,而牧羊人长辈们善良、坚韧、正直、吃苦的个性所烙刻在我血脉里的印迹,一直陪伴我后来行走这纷纭世界的千山万水,笑对红尘冷暖、江湖沉浮。
草原上的鸿雁每年去了又来,时光却如江河之水日夜奔流,永不回头。如今,故园荒草,残梦依稀,当年的牧羊人长辈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父辈们脸朝黄土、饱经风霜的那些岁月已随风远去,我自己也渐两鬓霜花。但是,在外多年的我,脑海里仍经常浮现这样的画面:夕阳下,上百只羊组成的队伍正走下山坡,一路滚滚而来,羊群或长或短的叫唤声,牧羊人响彻四野的鞭子声,不绝于耳,如同一曲命运的交响。而母亲,则在锅灶旁边忙碌边说:“放羊的人回来了,该开饭了。”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