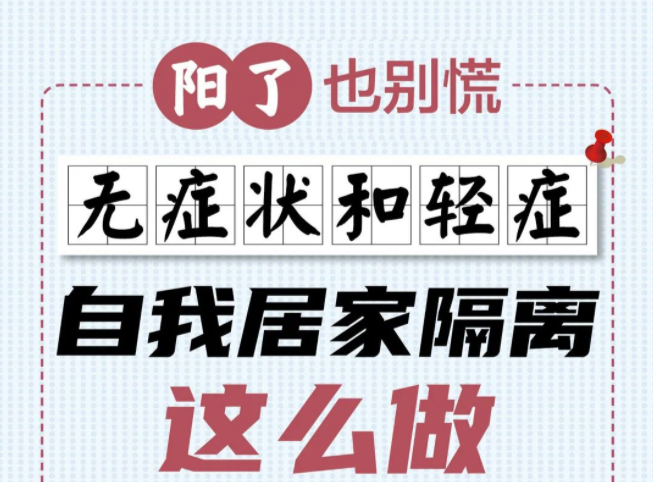□张斌(三台)
我的老家在涪江河畔,三台县刘营镇杨家碥村。滔滔的涪江水从村前流过,老家的香积山便和对岸的花园镇一水相隔了。
花园镇,旧称“涪城坝”,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涪城麦冬”的主产区,也是古梓州涪城县故址。“诗圣”杜甫寓居梓州时,曾作诗《涪城县香积寺官阁》: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阁迥添愁。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诸天合在藤萝外,昏黑应须到上头。这里的“春江”,就是涪江。“寺”,是香积山上的香积寺。香积山,古涪城县的后花园,山上稠木葱倩,鸟语花香,景色秀美,古人描绘香积寺“缔构雄丽,气象伟特”。而“官阁”,则是官方修建供游人休息的亭阁。
我的老家就在香积山下。童年时期,我和小伙伴们在涪江河里摸鱼,香积山上捉鸟,知道香积山上曾经有个香积寺,但已在兵匪动乱中被毁,唯有崖壁上还残留着一些摩崖题刻和遗碑。而河对岸的古梓州涪城县,更是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已经演变为一个地方小镇了。
但是,连通着古涪城县和香积山的那个渡口,却穿越千年时光,依旧守望在涪江岸边。
古渡的河道宽不过百余米,河水幽深,水流舒缓。在我小时候,要想去河的对岸,是要乘坐苏大爷撑的那艘渡船的。那是一艘一次可容10人左右的木船,船尾搭了一个竹编的拱蓬,是苏大爷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寒来暑往,苏大爷都住在船上,只要有人过河,苏大爷就会站上船头,挥动篙杆,稳稳地把人渡过河去。
后来,我长大了,读了书,知道了“诗圣”杜甫,知道了因避安史之乱入蜀的杜甫曾经“一年居梓州”,更知道了杜甫寓居梓州期间留下的诗作《涪城县香积寺官阁》。回到老家,我总爱徜徉在香积寺渡口,遥想在唐代某一个春天的傍晚,“诗圣”杜甫从涪城县城漫步而来,坐上涪江岸边的渡船,缓缓渡过夕照下的涪江,乘着暮色攀登在香积山的翠林小径间,望山下江水幽深,野鸭和白鹭在江面上悠闲地嬉戏,看四周林密木秀,掩映在树木藤萝间的官阁春意浓浓。不知不觉,天快黑了,诗圣加快了脚步,匆匆往上面的香积寺赶去。我在香积寺渡口流连忘返,总感觉诗圣离我那么近,就仿佛刚刚擦肩而过。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家出土了一块石碑,上刻“祇陀院新移亭阁记”,记叙香积山“六寺观”之“祇陀院”幽美的景致和增辟景点的经过,碑文落款:“大观庚寅五月初吉,梓州涪城县令赵宗尧记并书,权住持神照上石。”这位涪城县令赵宗尧在碑文中说,他与祇陀院住持神照和尚交情深厚,常往观澜赏景。赵县令去往祇陀院,自然也会从香积寺渡口过涪江而来。
依“大观庚寅五月初吉”年款,那是北宋徽宗年间,公元1110年。彼时,“诗圣”杜甫在唐朝过香积寺渡口登香积山,已逾300多年,涪城县令赵宗尧又在宋朝过香积寺渡口,前往香积山的祇陀院,两人在不同的时代,通过同一个渡口去往同一座山上揽胜,他们的脚步就这样在不同的时空里重叠在了一起。
千年香积寺古渡口,不知道成全了多少人的南来北往,却因为曾经渡过“诗圣”杜甫和涪城县令赵宗尧而让我肃然起敬,萦绕于怀。
物换星移,岁月流转,香积寺古渡口似一位慈祥的老人,在那里不辞辛劳,迎来送往。但是,他也有发脾气的时候。遇到夏天河里发大水,滔滔的洪流裹挟着树木杂物咆哮而去,渡船就只有停靠在岸边,随浪飘摇。河两边的人如果在涨水前去了对岸,而他们在对岸又没有亲戚可以投靠,就只有守在河边等待洪水退去。两边的亲人可以隔河相望,却是扯破嗓子也喊不应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为了改善两岸群众的交通条件,上游涪江河上修通了一座跨河大桥,刘营镇和花园镇往来的行人和车辆就再也不受河水阻隔了,而香积寺渡口的过渡人也越来越少。
这些年,下游涪江河上又新建了一座拦河水电站。今年暮春的一个周末,我回到老家,看到老家外面的河道里已经蓄满了水,河面变成了一汪平坦的湖,位于电站蓄水区的香积寺古渡口也已经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伫立在薄雾缥缈的古渡口,我久久不愿离去。时代的潮流势不可挡,香积寺古渡口的消失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但是,“诗圣”杜甫和涪城县令赵宗尧在古渡口留下的足迹却是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