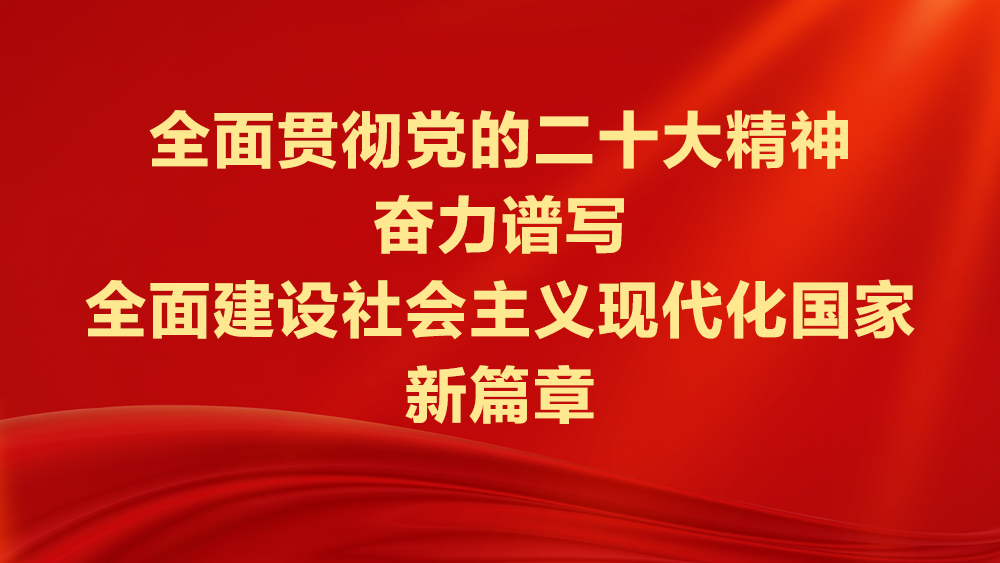□江剑鸣(平武)
棕树河是磨刀河支流罐子沟的一个小院子,因棕树多而名。它是我的生命降临之处,也是我父亲的生命归去之所。任何生命的降临和消亡都是必然的,但是,在什么地方降临或消亡,以怎样的方式降临或消亡,却是偶然的。“我从哪里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哲学命题太深奥啊!生命总要在一个具体的地方降临,又总会在一个具体的地方结束。棕树河迎来过许多生命,也送走许多生命。山坡上的杂花草树,春发夏长,秋萎冬枯。那些棕树,却青了一年又一年,因为,我那故去的父亲,魂灵永存在我心里。
父亲家里太穷,娶不起媳妇,只有当上门女婿,从老家大坪山入赘了罐子沟强姓人家。上门要改姓,但他没有改,还用早先的姓名。入赘人的子女自然随了母姓,我哥和弟弟妹妹都姓了强。
村里在大山里办个药场,让部分家庭困难且自愿前往的社员,整家迁去,种药材,当归、党参、大黄、川芎,但实际上是砍火地,开荒种粮食,让大家聊度饥馑的艰难。药场社员砍出几百亩火地,一把大火烧过,黑油油的肥沃土壤,可以种药材,更多的是种玉米,种洋芋,种黄豆。父亲一家就从棕树河迁去了,只留下青青的棕树在院坝边自由地生长。在药场干了两年,父亲又搬回了棕树河。他不像农村其他人那样老老实实待到生产队参加集中劳动挣工分。他只给生产队吆牲口,放羊,放牛。他还喜欢养狗,打猎,做小木活,淘河浪子沙金。
那时,生产队上缴公粮,靠人力背到公社粮站。罐子沟养有牲口,用牲口驮运,节省人力。父亲是赶马的把式。赶马人又叫作吆牲口的。生产队公粮缴完了,公社粮站又要组织运力,把公粮运送到二十里外的区粮站去。我父亲就留下继续吆牲口。
父亲特别喜欢养猎狗,侍弄猎枪,上山打猎。磨刀河的人叫他们为打鹿子。冬天农闲时,他去朝天宫大山后石坎水观一带买猎狗,买一种特别会撵鹿的窝前狗,出手就是几十元一条,居然一次买回两三条,常常被母亲指责。买回狗来,拴在棕树下,天天都能听到犬吠,倒也热闹。舍不得给孩子买衣服,家里没盐巴他都不管,但狗不能饿着。
不吆牲口的日子,父亲给生产队放牛放羊。我放寒暑假时回去,跟哥哥一起陪他。牛羊在山坡上自由自在地吃草,我们在沟边树林里玩耍,支鸟套,做弹弓,或者掏毛芋,挖山药。父亲指导我们,还给我们示范。我们套过相思鸟,套过画眉鸟,还套过松鼠。我特别喜欢毛老鼠的尾巴,毛茸茸的,光滑,暖和。我们挖回不少山药,可以补充口粮的不足,也可以炖肉吃,可惜那时候没有多少肉可以炖着吃啊!
1971年公路修通了,从生产队经过,有了拖拉机,不需要牲口了。生产队不再集中养牛羊。父亲成了闲人。暑假时我回去,见他在河坝里挖沙,在一个小船形物件里淘洗。他说在淘金。他给我看,小船底部木板上沾着一点点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黄色。他说:“这是猫猫金。运气好的话,可以淘到麦麸金,有时还能淘到瓜子金呢!”我对那种翻挖几大堆沙才得到那么丁点收获的事情不感兴趣,只管跟同村的孩子们跳进水塘里洗澡。
放寒假回去,看到父亲在棕树下支起木马,架子上横放一根木头,他正拿一把锛斧,在木头上砍挖。那锛斧的口子,寒光闪闪,晃人眼睛。我觉得父亲多么厉害呀!问他在做啥,哥哥抢着说,他在挖撮瓢和瓜瓤。农村撮粮要用撮瓢,灶房里舀水要用瓜瓤。哥哥说,父亲还会挖蜂巢,挖猪食槽呢。那是一种老式的养蜂木巢,两块木头,掏空中间再合起来。猪食槽简单,锯半边木头,掏空即可。但据说如果技术不好,挖的蜂巢不招蜜蜂,挖的猪食槽养猪,猪不长肉。四围大山笼罩在云烟中,云烟缝隙里可以看见山头的皑皑白雪。山沟里寒风刺骨,我都冷缩起了。父亲额头上却冒出热汗,说话时,呼出一股股白色气烟。他那圈黑色的头帕散下一缕帕头,搭在肩上。他放下锛斧,缠上头帕,披上那件已经分不清颜色的短袄,从腰上取下烟袋,坐在木马上卷叶子烟。他的手指,简直就是干枯树枝,每个骨节长个大疙瘩,手指手背都裂出大大小小的口子。我在心里疼啊!他划根火柴,点燃烟锅子,“啵嗤、啵嗤”咂几口,递过烟袋来,乐呵呵地说:“小子,来整一口?”
1994年春节后,棕树河房子后边的山坡上,青青的棕树下,多出了一垒崭新的土石。一个在大坪山出生的生命,在磨刀河罐子沟奔波近八十年后,融入了棕树河的泥土。白纸做的魂幡,在寒风中飘荡。看墓旁的棕树,那一身苍黑,不正是父亲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标志吗?树干上刻就年轮的累累刀痕,不正是老人满脸深深的皱纹吗?树顶上那青青的棕叶,不正是一个普通人坚韧倔强的精神和性格吗?
后来,腊月底和清明节,我回棕树河,都要去看看那些棕树。青青棕叶,生长旺盛,蓬勃向上,似乎正昭示着父亲普通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