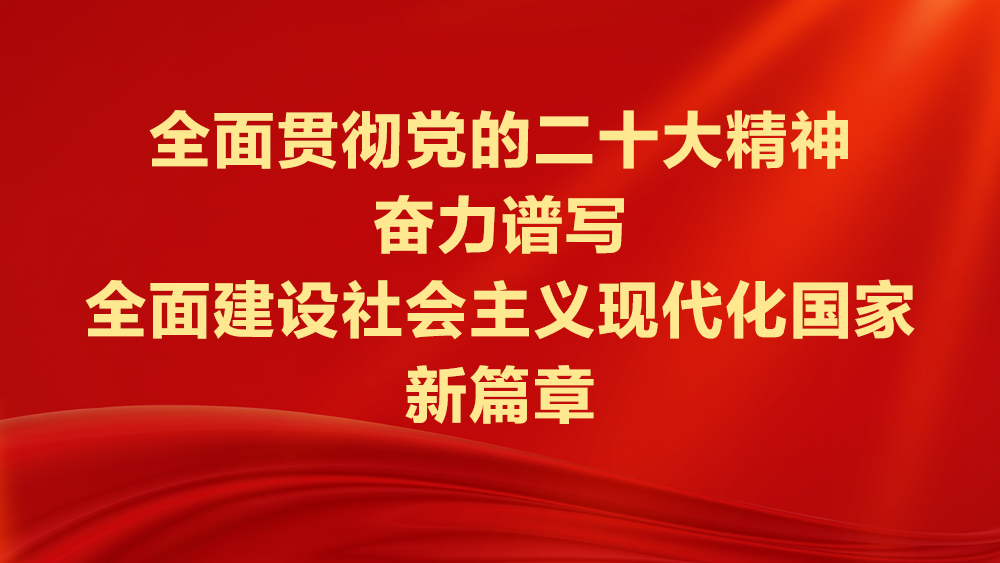□洞脚牛(绵阳)
今年是著名作家沙汀先生诞辰120周年。沙汀,原名杨朝熙,后改名杨只青(并用杨子青),1904年出生于安县安昌镇(现北川永昌镇)。沙汀与巴金、张秀熟、马识途、艾芜并称“蜀中五老”。
笔者因热爱沙汀先生作品而与沙汀之孙杨希结缘,交往中同感于沙汀先生的率真质朴,而为挚友,幸得近距离聆听他讲述爷爷的故事——
一
那是我儿时一个夏天的下午,爷爷外出理发后回省文联大院。守门的老大爷一时没认出来他,拦住不让进:“你是哪个?随随便便就想进来?”
“我是沙汀嘚嘛。”
“你是沙汀?我还是巴金呢!”
爷爷没有争辩,转身穿过巷子去找公用电话亭,请省文联办公室主任帮助证明自己是沙汀。省文联办公室主任急急忙忙赶来,说明情况,要门卫老大爷向爷爷道歉。爷爷赶忙说:“这个不能怪他,他没有错,错在我,出门没有带出入证。”随后,他还和大家说起了列宁与卫兵的故事。
爷爷1972年11月回到成都后,到1976年6月到西昌“上山下乡”前的那段时间,我在石室中学念书,和爷爷住在一起。爷爷十分宠爱我,给我买了辆转铃铛的永久牌自行车,我在玩伴们中间很是神气。这是我陪伴爷爷最多的时光,也是我成长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这期间也是我读书特别是文学作品最多的时候。爷爷的藏书很多,翻过一个窗户就是省文联图书室,那里藏书更多。我那个时候顽皮,经常翻窗户去找书读,成排的书架,一摞摞的书,让我很是惊叹,虽然很多书都读不懂但很是过瘾。
爷爷喜欢散步,这是他每天晚饭后风雨无阻的“功课”。日常不下雨的天气,就沿红星路、春熙路走一大圈。遇到下雨,就在院子或者房间里来回走动。爷爷身高大概有一米七,走起路来喜欢抬头挺胸收腹,而且走得很快。我身高约一米八,却经常走不过爷爷,落在后边。
一天,我在散步时又落在了爷爷身后。爷爷转过身:“你年纪轻轻的还走不过我咹?不过,走慢点也好,让灵魂跟上。”
“爷爷,啥子叫让灵魂跟上哟?”
“这是印第安人中流行的一句谚语:人要走得慢一点,好让自己的灵魂跟得上自己的步伐。意思是叫我们做事不要慌张,要勤于反省、检讨自己。”
爷爷早在1927年就在成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爷爷说,那个时候,信仰可以战胜恐惧。我信仰共产主义,我不怕!
第一次听敬爱的爷爷谈到“信仰”,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心潮澎湃,激动得好像身上的毛孔都打开了。爷爷后来回安县筹建共产党支部,在艰苦的条件下一边躲避追捕,一边坚持创作,写出了以长篇小说“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作品。
二
爷爷和艾芜是生死之交,被称作“文坛上的双子星座”。他俩一起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现成都大学师范学院的前身)读书;1931年夏天在上海街头偶遇,同年11月联名写信给鲁迅请教小说创作(鲁迅后来将来信和复信以《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为题发表);1934年一起当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后来两家人又一起生活在成都同一个院子里。生活年轮的交集是一方面,共同的信仰、价值观才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两人于1904年同年出生,1992年同年逝世,成为中国文艺界不朽的传奇。
爷爷经常给我讲汤爷爷(艾芜原名汤道耕)的故事,包括艾芜在南行旅途中吃过的苦头。艾芜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书、纸和笔,用细麻绳系着瓶颈的墨水瓶被挂在胸前以防被打破。在小客店的油灯下,在树荫覆盖着的山坡上,他随遇而安,一坐下来,就把小纸本放在膝头上,抒写见闻和断想。爷爷还讲到艾芜在流浪途中,肚子饿极了想进餐馆吃饭,又害怕钱不够,被店老板用板凳顶在头上、跪在地上当街示众……爷爷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汤爷爷太不容易了”,对老友的敬重、疼爱溢于言表。
作为文坛前辈,爷爷付出的心血最多的是长篇小说《红岩》。对这样一部“主旋律”作品,大都认为不容易改好,爷爷却认为经过加工可以成为一部好作品。《红岩》原名《禁锢的世界》,调子有些低沉,主要描写禁锢在集中营的生活,很少接触到全国已临近解放的大好形势,这是作品初稿最大的不足。爷爷多次找到作者罗广斌,和他们恳谈,逐章讨论、修改。作品出版前,几位作者讲:“沙老,这部作品是您花了这么多功夫指导弄出来的,得把您的名字署在前边。”爷爷严辞回绝:“这是你们的作品,怎么能署我的名字呢?”
《红岩》从准备到成书,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写了三百多万字的稿子,返工过三次,大改过五六次,1961年12月第一版引起强烈反响,仅仅四年时间就发行了五百万册,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2019年,《红岩》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爷爷关心、帮助中青年作家的另一面,是他曾不厌其烦地指导修改并撰文推荐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作品于1980年出版;1981年,北影厂和八一厂同时拍摄了同名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很少见的“撞车”事件;在1982年举行的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排在六部获奖作品的第一位。
爷爷一再告诫周克芹,希望他能经受住成功和荣誉的考验,不要骄傲,不要背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本书的“包袱”,而要更上一层楼,坚持在生活中与群众同甘共苦。
三
读书,是爷爷一生的习惯,而且读得入迷。他会在看书时突然哈哈大笑,而且是那种爽朗的、持续很长时间的大笑。
有人说爷爷受契诃夫作品的影响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爷爷是“中国的契诃夫”,这话不假,爷爷到了晚年仍然喜欢读契诃夫的作品。一天,他正读着契诃夫的作品,又突然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还连声称赞:“写得好,写得好,写得实在是好!”
年幼的我不解:“爷爷,契诃夫是哪个哦?”
“吔,契诃夫不简单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军队快攻到苏联的首都莫斯科了,斯大林专门在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在红场阅兵讲话鼓舞士气,其中就讲到了列宁、普希金和契诃夫这些名人。斯大林的讲话结束后,红场上口号声、掌声连成一片,全场都在高呼‘乌拉!’这次阅兵后部队直接奔向战争前线,打败了希特勒的军队。”
顿了顿,爷爷接着说:“契诃夫的作品,在短小精悍中体味辛辣讽刺……创作离不开对环境的熟悉,我跟你讲,在我的老家,哪怕不出门,有人打个喷嚏,我就晓得他在想些啥子,能猜到他家里有几亩田地……”
一天,我问爷爷:“爷爷,你是啷个写出那么多文章的哦?”
爷爷回答:“写东西要简明扼要,真实感人,要通俗易懂,有个性,让人一看就晓得是你写的。”
爷爷对党忠诚,对爱情忠贞不渝。我小时候顽皮,有时候调收音机频道,会闹着玩儿收听不同频道广播电台节目。遇到爷爷在场,他就会严肃的告诫:“希儿,不准收听不该收听的哈。”爷爷和奶奶黄玉颀自由恋爱结合,一生相濡以沫。不幸的是,奶奶在1964年因病去世,那时爷爷不到60岁。二十多年间,为爷爷做媒续弦的不在少数,但爷爷一律婉言谢绝。那张奶奶在北京北海公园一棵柳树下系着围巾的照片,一直放在爷爷的床头,陪伴到他生命的最后。
1992年12月11日,爷爷得知老友艾芜几天前逝世的消息,欲哭无泪(因双目失明眼泪流不出来,在眼眶里打转),悲痛欲绝,连声哀叹“道耕太苦了”,口述《有文皆苦无食不酸》一文,极尽悲悼之情。14日,爷爷因悲伤过度逝世。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