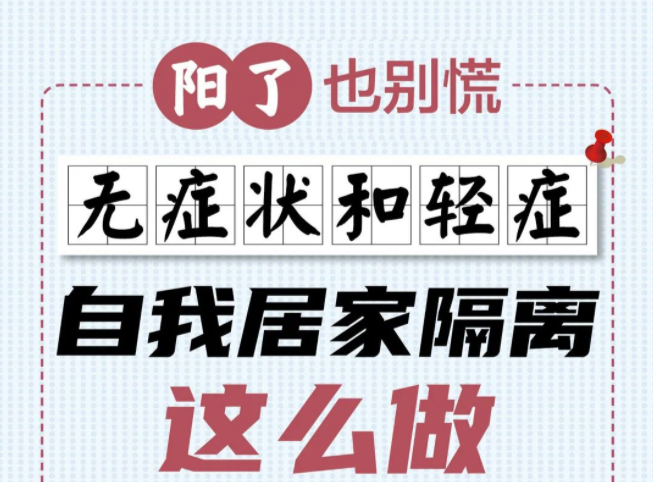□汤飞(绵阳)
在乡下长大的孩童,谁的夏夜记忆里没有一床竹垫呢?
它的模样是长方形,长达四五米,宽近两米,两条短边夹着弧形的竹壳,便于裹卷。竹垫白天是农具,平铺于院坝,稻谷、玉米、小麦、菜籽、胡豆等轮流躺在上面,沐浴阳光,痛痛快快地出一通汗。晨出昏收,其间还用木耙子翻晒。它忠实地呵护着农家的丰收希望——在粮仓填饱肚子之前,丰收之曲随时都有出现休止符的可能。这绝非危言耸听。
我最喜欢收粮食了。因为可以将它们当作原料,以木耙子作笔,描绘各种各样的图案,书写歪歪扭扭的文字,轻轻一抹,又能重来。竹垫一空,立即裹成筒状,以免占地方。别人的成果又细又紧,而我的则又粗又松——方法和力道不对,不但难看,而且连绳子也捆不上。
由于次日还要继续使用,竹垫一般就卧在阶檐旁边。到了傍晚,它化身为坐具。盛夏时节,屋里闷热,大家不约而同地端着饭碗在外面吃,竹垫正好做凳子,比正儿八经的饭桌更受欢迎。埋头扒两口饭,抬头望望天边的火烧云,听着倦鸟归林的孤鸣,向晚归的人打招呼。兴许一顿饭尚未吃完,天空已“退烧”,化作淡青色,很快将要更换晚装。
夜的墨滴在天地间晕散,染黑了一汪清水。繁星缀在幕布上,随轻风浮动。邻居们三三两两地团坐于宽敞的院中乘凉,各摇一把扇子,无需点灯。大人在夜色的掩护下从脑海里打捞陈年旧事,或者日间因忙碌而无暇摆谈的新闻。草丛中的蛐蛐、田里的蛙儿争相赛歌,谁也不肯示弱。
这时,竹垫成为孩子的玩具。骑在上头蹦高,感觉犹如拖拉机的驾驶座——那个座位用鼓气的轮胎制成,经常能看见司机因道路不平而抖得老高,让人担心他一不小心会飞出去。抑或张开双臂行走其上,看谁顺利通行的次数最多。又或视为小船,手握木棍左划划、右划划,还故意装作遇到风浪,左摇右晃、前俯后仰。名曰纳凉,其实玩出了一头汗,对长辈“停停耍(安静)”的命令置若罔闻。
玩得累了,躺在竹垫上张望星空。将相邻的几颗星想象成某个形状,然后指给头对头躺着的伙伴,如果他迟迟找不到,便可光明正大地嘲笑。万一人家
有更精妙的解释,难免被比下去。某人问:“天亮以后,星星去哪儿了?”课本里缺少相关的答案,意味着不会考试评分判对错,怎么回答都行。有人说跳进海里洗澡去了,有人说下课回家了,有人说它们拉上了名叫“云”的窗帘。大伙儿咯咯地笑作一团。
偶尔发现有一粒星点在缓缓移动,于是惊呼且目送,生怕失之所在。结果后面跟着轰鸣声,原来是飞机。这也算夜间一景啊。
大人的交谈有极好的催眠效果,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把竹垫当成床,沉沉睡去。梦中翻身,跌落在地,茫然不解身在何处,听到熟悉的话语声方觉心安。
如遇月明之夜,小小山湾别有一番景致,恍如仙境。目光越过连片的稻田,直达对面的庭院,那儿亦有同样的一群人。喊一嗓子,还能得到回应,隔空对话惹得长辈笑话。
夜深了,人们各归其屋,家乡成了梦乡。只是当时的我还不明白,自己再难拥有那样的暑夜体验,而家乡终于变作梦里的故乡——唯有梦是归去的捷径。竹垫早已被层层叠叠的时光埋藏,下落不明。
编辑:李志 校对:郭成 审核:刘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