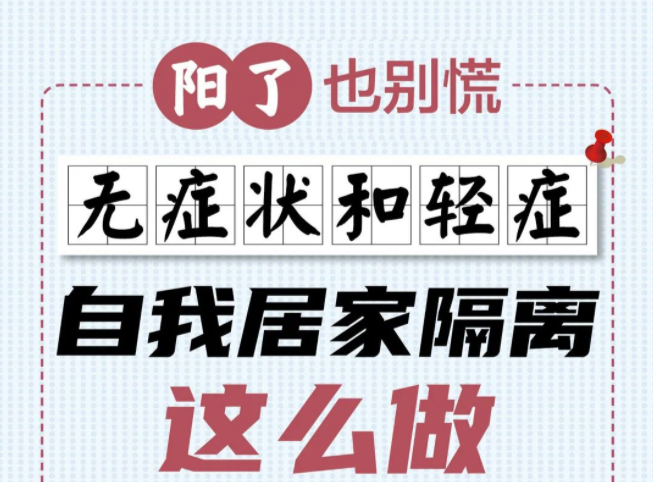□味辛(三台)
张大娃家新建大瓦房的时候,柿子湾里很多人家还住着茅草房呢。张大娃家新建的大瓦房是三间正房还挂了两间偏厦子,十分气派。
那还是大集体时代,张大娃的父亲是个赤脚医生,一边给人看病,一边在生产队劳动,家里的经济条件自然要好些。但是,大瓦房建成不久,张大娃的父亲就在一个晚上提着马灯去出诊,掉下山崖摔死了。
那时候,张大娃正上小学三年级,他的弟娃马上又该上学了。张大娃的父亲死了,娘又有病,家里实在供不起两个人读书,娘就跟张大娃商量,说,你要大一点,回来还可以帮娘挣点工分,就让你弟娃去读吧。张大娃就断了学业,回到家里,跟着生产队的大人一起翻苕藤、摘棉花,干些手脚活路。
稍大一些,张大娃就去学了瓦匠。这时候,住茅草房已经会让人看不起了。柿子湾还住着茅草房的人家都在想方设法建大瓦房,瓦匠还是一个吃香的行当。但是,人们往往要等到冬天才会修房造屋,因为其它时节,要么是农活太忙,要么是雨水太多。张大娃做瓦匠,从踩瓦泥、拉瓦坯,到做瓦,一个冬天都在和稀泥打交道,双手冻得跟红萝卜一样。挣到钱,都拿回家,给娘抓药用了。
后来,大集体解散了,土地下放到户。张大娃也已经成长为一个壮劳力,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张大娃娘俩种着自家的承包地,收获的粮食不仅可以让一家人温饱不愁,还有余粮卖钱。
张大娃的弟娃在学校读书,越往后读,书学费却是越来越贵了。娘就用家里的粮食饲养鸡鸭和猪,卖了钱,供弟娃读书。逢年过节,张大娃说,娘,杀个鸡吧。娘却黑了脸,说,你弟娃读书要用钱呢。娘的病重了,张大娃说,娘,住院吧。娘还是说,你弟娃读书要用钱呢。
弟娃也争气,后来就考上了大学。弟娃是柿子湾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不得了啊,八方来贺。那阵子,娘开心得合不拢嘴,到处都听得到她爽朗的笑声。
弟娃上大学后就有人来给张大娃提亲了。张大娃心里喜悦,去找娘拿主意,娘说,你弟娃上大学正用钱,你说媳妇儿也要用钱,还是等你弟娃把书读出来再说吧。张大娃就只有埋头种地。弟娃读完大学,在城里有了一个体面的工作,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落后了,张大娃好不容易才娶到媳妇儿,安下一个家。
这些年,柿子湾人纷纷外出打工,挣了钱,扒掉土墙瓦房,新建了砖墙房,那新建的房子红砖碧瓦,在阳光照耀下十分气派。张大娃也想出去打工挣钱,把砖房建起来。但是,娘说,你出去了,家里那么多土地靠哪个种?靠你媳妇吗?靠你娘吗?张大娃就只好在家种地。只是农资越来越贵,张大娃勤扒苦做,家境也没有好大变化。
弟娃工作几年后,在城里按揭了一套住房,又娶了一个城里的媳妇儿。逢年过节,弟娃带着城里的媳妇儿回来,娘远远地去迎接,一路有人招呼:大学生回来啦?娘就一路乐呵。
后来,娘的病越来越重了。娘卧床不起的时候,说,柿子湾家家都住上砖房了,我二娃在城里也住上了楼房,我大娃要是有出息也修几间砖房让我住几天,我这辈子也就满足了啊。张大娃听了这话,心里刀剐一样难受,却只有唉声叹气。
娘走的时候,弟娃还在遥远的城市里。那时节,地里的麦子已经现枇杷色了,娘的尸体在家里停了三天,弟娃也没有赶拢屋。大家都说,这种气温不能再等了啊。张大娃只好请娘入了棺。
送走了娘,张大娃已经迈进五十岁的门坎了。张大娃牢记着娘的临终牵挂,一心想拆掉家里的土墙瓦房建砖房,但是,出去打工吧,没有技术,体力也在走下坡路,张大娃就只有在柿子湾守着土墙瓦房犯愁。
却赶上实施乡村振兴了。先是修通了入社到户的水泥路,然后是遍山栽植果树和花草。春天里,烂漫的鲜花招蜂引蝶,秋天到,香甜的果实缀满枝头,吸引了大城小镇里的人来柿子湾赏花摘果,一拨又一拨,络绎不绝。
那些远来的人赏花摘果累了,他们又到农家小院里去歇脚喝茶,吃农家菜。柿子湾家家都是砖房,张大娃的土墙瓦房就格外引人注目。大人们带着他们的孩子到屋里屋外参观,感慨着他们当年也是住着这样的房子长大。他们又进一步晓得了张大娃至今还住着这土墙瓦房的原由,更是受到感动,就拍了视频在抖音、朋友圈里宣传,张大娃和他的土墙瓦房就成了网红。
张大娃家的人气越来越旺,他整天忙碌于他的果园和农家乐,收入与日俱增。但是,他却不再着急拆掉他的土墙瓦房了。这座柿子湾最后的土墙瓦房就那样固执地屹立在大家的视野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