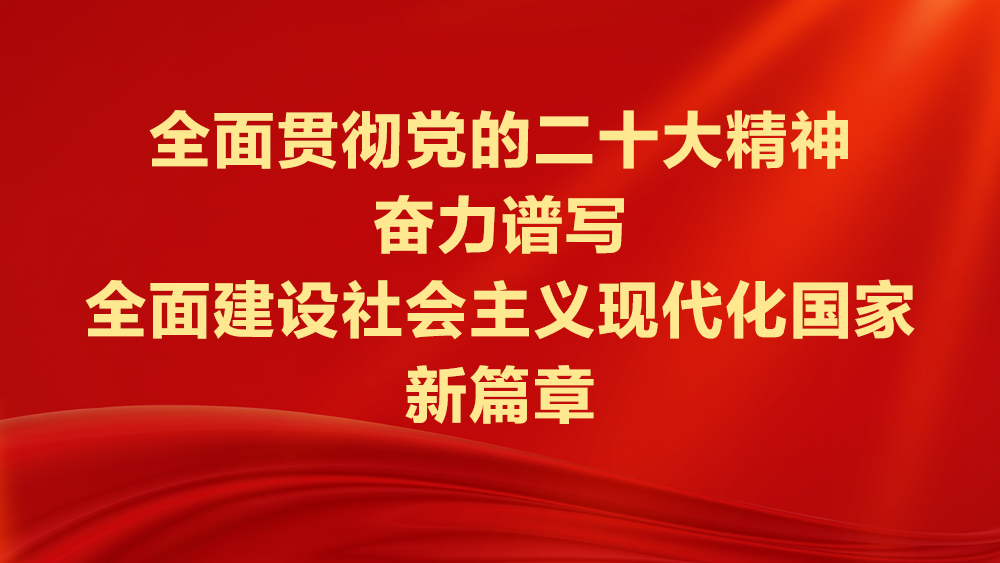□李勇鸿(成都)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夏天的夜晚,月光很明很亮,照亮了村子通往镇上的山路,也照亮了父亲。那夜,一路上,我每次抬起头,月光都在父亲肩膀上跳动着,闪着银色的光亮,我不停喊着:“爸,歇歇吧”。父亲却头也不回地继续拉着架子车说:“不累,翻过这个山梁就到家了,趁着月亮没有下山,快走吧。”
那一年,我高中毕业在县城有了一份工作,父亲却退休当了农民,和母亲一起耕种着家里的十几亩地。那时候,全村人几乎都住在窑洞里,持续几十天的连阴雨,许多人家的窑洞开始倒塌。过完春节,政府号召村民搬出窑洞,建砖瓦房,我们家也划了一块新宅基。周末回老家,我同父母一起去那块地里看过,父亲蹲在那块地边,筹划着哪里建主房,哪里建门楼。一家人都期盼着十几亩小麦当年有个好收成,卖了钱筹备盖房子的材料。谁知,本来长势很好的麦子就在即将喜获收割时遭遇了一连七天的阴雨,金黄金黄的麦穗在雨中发霉变色,麦粒也长出了麦芽,全家人的希望一下子成了泡影。
那些日子,父亲经常坐在窑洞门前抽着烟,呆呆地望着天空。窑背上有一条路,路边竖着一根电线杆,我家里的电线就是从那根杆子上接的。进村出村的人经常站在电杆下和父母打招呼。一天,一位大伯从外村榨菜油回来,说邻村那家开油坊的生意特别好,多亏去得早,排了半天队才轮上,不然就要等到天黑了。父亲突然站起来了,看着那空中电线笑了。
那些天,父亲每天晚上看电视就只看广告,终于看到了一则小型榨油机的广告,他把厂址和电话抄写好,托人带给我。还专门到村上的小卖部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去城里看看。一个周末,我搭朋友的卡车专门去了一趟西安,以800元的价格买回了一台小型榨油机。此时,父亲也托熟人在镇上联系了一家专门出售旧电机的门市,提前去了那里付了款,说好将一台10千瓦的旧电机用300元买回。
就是那个夏天的夜晚,父亲和我要用架子车去拉回电机,因为那天修电机的人白天外出,说好晚上才回去。我们从家里走时天已黄昏,父亲仔细检查了架子车的车胎、车箱板上铺垫的麦草垫和用来捆绑电机的绳子。等确认一切无误时,他对我说:“走吧”。我拉着车子出了家门,这时,他又回头去了家里,等父亲再出家门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
家离镇上要走二十多里路,虽然是宽敞的公路,但要走一段土路才能上柏油路面,下坡又上坡翻一个大沟上塬,才能到达。去时,由于是空车,走得很轻松,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镇上那个电机门店,店主人认真地给我们调试好,又帮我们装上车,父亲用一根很长的尼龙绳将电机五花大绑捆在车上,然后用手摇摇,确认很结实后,给那人又递上一根烟,才招呼我回家。
平路和下坡的路上都是我拉着车,父亲在后边跟着。可到了沟底的水坝上,父亲让我停下歇会,我抬起头看到圆圆的月亮从山尖正在升起,父亲说,刚好,今晚有月亮,就不用手电筒照路了。说完,他走到我跟前又说,要上坡了,我拉车,你到后面推着吧。说着父亲就将自己的外套一脱,搭在架子车的辕杆上,自己拉着车子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我一路小跑追上车子,奋力地推着。夜晚的公路上非常寂静,月亮已从山尖升到了半天中,明亮如水的光亮照在山路上,地上的一颗小石子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转弯,前面要爬一个陡坡,父亲的身体弯曲着,那条搭在肩膀上的带子在他的身体上陷入很深,月光在父亲肩上跳跃着,闪动着,肩膀上的汗水和那古铜色的肌肤,在月光下更显得有力而伟岸。终于上了坡,村子里的人们已经睡去,夜色中,只有我们家那孔窑洞还亮着灯火,那一定是母亲还在等待着我们父子归来。
在随后的日子里,每到周末回家,远远的,我都会看到我家门前有来往榨油的乡亲们。走进家院,那台榨油机的“突突”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父亲总是低着头在又闷又热的屋里操作着那台小机器,他的肩膀和背上总有汗水,可他那布满沧桑的脸上却写着幸福的微笑。过了两年,那台榨油机完成了使命,被父亲卖了废铁,而我们家也终于建起了三间瓦房和一个小院。父亲在院子里建起了小花园、鸡舍和小狗窝,后院还弄了一块菜地,一年四季精心呵护着小院的新家,我们兄弟姐妹每次回家都会感到温暖可亲,每次离家总是依依不舍。
几年前,父亲患重病去世,我们只能带着母亲离开老家。从此,看守老家的,便只剩一把生锈的铜锁。今年端午节回老家,当我推开小院的门时,昔日的记忆像潮水般涌上心头,父亲生前音容笑貌、每个细节浮现在眼前。夜里,我躺在父亲曾经睡的土炕上,忽然,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就像多年前我和父亲走在山路上的月光,一样明,一样亮。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