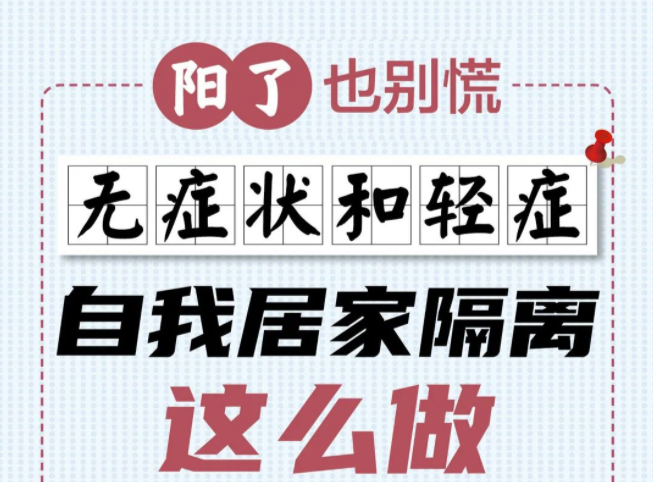□ 宋长丰(绵阳)
未读此书时,书名已吸引了我。《当时酣醉》理解起来容易,但要写好却非常困难,是一大挑战。难在何处?先卖个关子,容后道来。
但很明显,困难也许作者所未料到,但困难恰巧是艺术出彩的垫脚石。六十年前,杨绛先生的论文《艺术是克服困难》就说了,创造好的作品,“好比一股流水,遇到石头拦阻,又有堤岸约束住,得另觅途径,却又不能逃避阻碍,只好从石缝中迸出,于是就激荡出波澜,冲溅出浪花来。”《当时酣醉》能否冲出美丽的浪花呢?拿到书后,我便迫不及待寻找了起来。
尽管我的兴趣在文艺评论,但我不喜欢用主题鲜明、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等放在哪里都合适的词语,也不愿意用一些隔靴搔痒的表扬或批评,而喜欢以文章本身的意境所获得的感受来谈论。这,是受到钱钟书先生的影响。
说来也巧,我曾在报社工作多年,与作者虽有同事之实,而无半点交集之情,未识其人。但书中所涉及一二人物,却也有点不大不小的瓜葛。如去北京发展的经济部邹主任,他儿子和我是小学同学,又如文中出现的游仙报张记者,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报道过我小舅马经义的“《红楼梦》梦幻结构说”。我与绵阳记者的缘分,还可追寻到千禧年之前,绵阳广播电视报的张记者,那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访,不过20多年再也无缘相见。
此书犹如故事会,一口气就可以读完,浅进直白中往往蕴含无穷意趣。如“散落”二字,写散在天涯各处的朋友,性情各异,寻常眼中也不过寻常生命,需有慧眼不可。擅长写古诗的豌豆,“无音通塞远,流年起荒烟。”这不是盛唐律诗格局,也不是喜欢说理的宋诗,倒非常像四言向五言过度时期的淡雅恬静。可是豌豆在做的是销售工作,我立即旁边批注:我也不忿,挣钱事人人都会,只不过有多寡之分,如此文艺之才,能有几人?在读到《冀鸭子》时,冥冥中总有一种感觉,此人恐寿不长久。这不是我能掐算,而是作者叙述中隐约有此之风,冀鸭子长袖善舞,又懂艺术,人才凛凛,作者描述全用烘云托月之法,擅用反衬。而D长风桌间嬉笑怒骂,让女性朋友看出来这是真正的好朋友,不禁让人想起阮籍,喜欢去隔壁美妇家喝酒,喝完就睡。这是发乎情,但不是止乎礼义,魏晋人不需要让礼仪来克制自己,而是心中本身无邪念,何须克己复礼?更有趣者,王小二请市长参加婚礼,先在报纸上发邀请函,而市长真的到场祝贺,送了一大堆母猪产后治疗一类的书籍。中文系某某赴宴,席间鼾声如雷,酒量不大却好酒,大有竹林之风。
作者因喜爱而去北漂,走南闯北,好不痛快。赴京前,打的追火车自是难得的往事,而坐着汽车去拉萨,则更是铭刻心骨的经历。不仅是路途跋涉,而是遇到了一段难忘的感情。吉米,这个在开篇文章中就出现的一闪而过的名字,却是收尾压卷的人物。万千中人,他是其中之一,而后又成唯一、独一,不经意间以此人始,刻意之中又以此人收,大开大合,真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往事已飘散,故人也已远行,读罢吉米故事,油然而生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本以为这禅意是王摩诘的句子,其实他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阅读的展开,作者父亲不断在文中出现,5·12成为一大关节。初中时候和父亲一起修县志,有苦也有乐。作者追问生命的本源,尽管没有结果,但在与女儿的生活中,我们分明已看见一股勃勃生机。生死、有无、虚实,本就是中国艺术与哲学探究的终极命题,十多年前,我爷爷去世时,我也有类似的追问和伤感,从今往后再也见不到了,不能对话了,这刹那间的生死成为永恒的遗憾。我们在述说这些事情时,纸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背后大浪滔天的情绪。
书中还有零星的艺术感悟给予我以启示,如读出《水浒传》中李逵失眠。我小时候熟读名著,却都被火热的情节吸引,根本没有注意这等细枝末节。直到最近系统阅读美学书籍,才知道小说评点派,如叶昼、李卓吾、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关注了很多小情节,可谓“闲笔”。闲笔淡淡,写尽生活悲欢。更令人有所获的是,李逵失眠的原因不是牛肉吃多了不消化,而是听到欺男霸女的故事,担心人家的安危。李逵这种黑大汉,绝不是那种假打的怜香惜玉或看上美女要留下好印象,恰巧是他天生中的一种憨厚、本真,打抱不平,自出胸臆。其实,作者喜欢结交的,恰恰是真性情人物。吉米可以看蚂蚁搬家津津有味,其实就是本色,连古板的理学家程颢都说喜欢刚孵化出的小鸡生机盎然,又何论当代精神自由的我们了。
最后,再说说我认为的困难,也就是冲溅出浪花所遇的那块石头。“当时”虽是白话,却也是文言常用一词,多见于诗词,如“当时年少春衫薄”“当时明月在”,而最为人熟悉的,就是清代著名词人纳兰的“当时只道是寻常”。王国维评价说,因词人天真烂漫,未染中原习气。李后主将词规格提高,数百年后,清人而能谈宋调,能将词意境再次拓展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在我看来,曹寅擅诗有唐韵,纳兰填词则达宋境,文坛双璧,风头一时无两。再说“酣醉”,此种微醺迷离之态而能成为作品,放在上古社会,东西文明都不会待见。柏拉图以维护神权为宗旨,定会将此书连同诗人们一起赶出理想国。而孔孟荀都高扬人文理性主义,与道德伦理关系不大的文学也不会给予好脸色。如孔子说武乐尽美,却未尽善。放在中世呢,文艺复兴或魏晋时期,虽然文艺足够自由了,但毕竟是各种文艺形式、理论的野蛮生长期,《当时酣醉》稍不注意,便会长期埋没。而到如今,当尼采也专门总结“酒神精神”,人们也能接受各种艺术时,又遇到新的问题,那就是买醉太容易了。你的酣醉就真的具有艺术性吗?真的能在千篇一律的微醺中构筑一幅审美的意象世界吗?能像陈与义那样,痛饮达旦后有一种轻微的美,“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或如苏东坡那种愁肠,“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吗?
很明显,是有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文章中很少提到自己喝酒,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是清醒的。证明她所说的酣醉,不是来自于酿造的酒,而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己的审美观照。这不同于陶渊明饮酒后的恬淡悠然与忘我,也不同于李白狂醉后乱把白云揉碎,反而有一点禅意、禅境。人生虽有逆旅,但作者性格豁达,便少了一点忧郁,或者很快抽离出来。
此书不是枯燥难解的理论,没有语言逻辑上的故布迷阵,所以阅读起来轻松而便捷。我只不过做了一次导游,帮助读者找了几朵美丽的浪花。漫游书中,真是“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扬。”(尼采《悲剧的诞生》)细细把玩,与此书最相似的意境,当属一位不太知名的唐朝诗人曹唐所云:“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见当时劝酒人。”其实书名出自七绝圣手“当时每酣醉,不觉行路难”,毕竟,那会儿已然酣醉。复醒时(不是喝醉是自醉),一切皆成过去,抚今追昔,瞬间即永恒,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遂有文集《当时酣醉》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