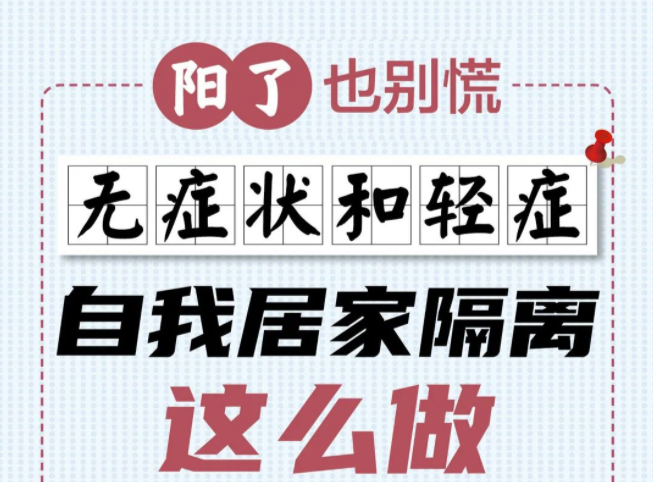□郭发仔(成都)
按民间的说法,惊蛰一到,“春雷惊百虫”,那雷声应该如战鼓,把硬了一冬的冻土敲碎,那些蛰伏得腰酸背痛的虫蛇也是时候出来活动活动了。民间的很多说法都是经验之谈,老辈人一代代总结下来的,我想是没错的。《大戴礼记·夏小正》中说:“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又名“启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戴氏所说的蛰虫惊而出走,应是确信无疑的了。惊蛰之时恰逢九九艳阳天,春暖大地,雨水润泽,万物萌发,所有蛰伏的生命都惊动了。其实,有无雷声并不重要,惊蛰就是时令的雷声。
前些时日还淫雨霏霏、凄风惨雨的,那些枯树干草在雨里蛰伏,默不作声,仿佛忍受一种伤到深处的痛。过了惊蛰,天空疏朗起来,太阳心情好得像醉了一场酒,连续几天都出来溜达,连光芒都有些发烫。阳光是金黄色的,很亮,很尖,从高空泻下来,穿过疏疏朗朗的树梢,落在马路上,洒在草地上,铺在水面上,一股不易觉察的热气腾起,嘶嘶有声。衣服感觉穿多了,后背的毛孔里渗出热气,滋滋地燃烧。半空里,一只白鹭斜飞而过,翅膀里夹着风,风里卷着泥
土的清香。谁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从风声里,可以感受到白鹭的亢奋,它一定是得到了大地的讯息,急着去告诉它的每一个家族成员,或者同伴。不止白鹭,镜湖里的小鸊鹈不知何时也出现了。三五只,五六只,比去年多了些,个头也大了许多。它们像小鸭,又像小鸟,在水里扑腾追逐,把平静了一冬的镜湖都吵醒了。是的,白鹭也好,鸊鹈也罢,它们都得到了一种普天同庆的讯息,听见了一种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号令:春天爆裂的声音。
李花、桃花早开了。不过,娇嫩欲滴的青春是在雨水里度过的,除了掩面而泣,发不出更多的声音。此刻,花瓣稀稀落落,在太阳下没了光泽,红的薄了,粉的白了,白的淡了。枝叶是尖尖的新绿,茎脉里饱满的汁液也是绿的,在微温的阳光下煨着,似乎可以听见轻微的沸腾声。“陌上杨柳方竞春,塘中鲫鲥早成荫。”水还有浑浊,鲫鱼是看不见的,但陌上竞春的杨柳有些招摇,原本枯瘦的形容有了绵软的鹅黄,千万条丝绦垂下,在风里摇摆,婀娜隽秀如浴后梳妆的新妇。
墙角处,一只蜈蚣从缝隙里爬出来,长长的触须左右探视,有些迟钝。它好像没完全清醒过来,纵有千足,也走不快。也许它听见了雷声,也许它听错了,是泥土里的蚯蚓一直在掘着土,是草丛里的蟋蟀哼哼唧唧叫了几夜,是地鳖虫的屁放得太响了,臭得难受。蜈蚣出来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声音都瞬间消失了,但总在耳边萦绕。其实,蜈蚣还听见了自己身体的声音,一节一节地在拉伸,在拼接。在这个时节,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在勃发,让所有的一切都发出生命的呼声。
“九尽桃花开,春耕不能歇。”桃花在九九时已经耗得没耐心了,开得毫无生气。土地却一条条蓬松,蒌蒿满地芦芽短,荠菜、苦丁菜、马齿苋长出来了,根茎在土壤里到处钻。在南方的乡下,此刻的空气中充盈着田野里的芳香,有农人扛着锄头下地,刨削田埂,整理弃土,收拾荒芜,雪亮的锄头发出一道光,毫无规律的钝响总跟不上有节奏的动作。水田里,耕田机在穿梭,啪啪地躁响,把本就有些膨胀的空气震成了碎片,落在粉蝶飞舞的油菜地里,落在水草葱嫩的小路上,落在村妇挽起袖子露出的白胖手臂和胳膊上,嗡嗡的、唰唰的、啪啪的,撞击在楼层的新墙上,发出一种无法辨识的声响。沉闷了一冬,整个村子都醒了,也在响。不过,在城里是没有春耕图的,只有菜市场的老头老太太,提溜了一些新鲜的蔬菜,还有一些野菜,用满是泥腥味的粗糙双手递过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乡野里的春天,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时不我待。
天气很不错,总有人嚷嚷要在周末去看花。想去,但总觉得精气神少了些,犯困,夜里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不见。人与百虫无异,蛰伏一冬,抗拒了酷寒与低温,体内的元气消耗无多,春发季节,体内虚空表征为口干舌燥。中医讲究药食同源,这也是民间经验。一盘春笋、菠菜,一碗鸡蛋炒毛葱、水煮芋头,粗粝的食物可以唤醒倦怠的脾胃。加上适当运动,以健壮的体魄搭起抵御季节侵袭的防线。
惊蛰吃梨,“梨”“离”同音,吃了便远离病患。乡下老人是这么说的。其实,寓意总是好的,梨子性寒味甘,可以养肺止咳、滋阴清热,对于祛除春的燥火大有助益。人是万物之灵,对付惊蛰,办法总比问题多。
咕咕——咕,沉闷的声音从高大的樟树上传来。不是雷声,而是沉睡了一冬的斑鸠,被春天的气息唤醒了。
惊蛰过后,一切生命都发出了新生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