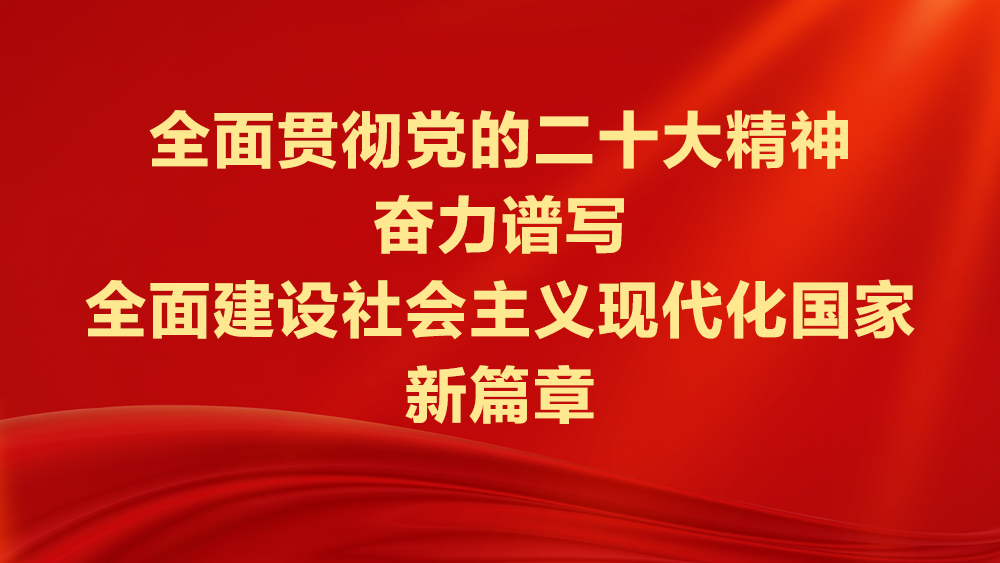□蒋晓东(绵阳)
午后的阳光下,一只翠鸟歇在我的脚边。它看着我,我看着它。不是对视或者对峙,而是相望。一时间,有一点安静。
冬天没有想象的那么寒冷。每个有阳光的午后,我都会去河边散步,感受阳光,领略大自然的赐予。
翠鸟也许不叫翠鸟。但凡有颜色的鸟,都会被我叫翠鸟。翠鸟是从河的水面上向我飞来的,因为它只有拳头那么大小,尽管它的翅膀是展开的,我也看不出它有什么样的身形。但是我感觉到了它身后的剪影,扑簌簌闪烁出了一串阳光。也许本来就是太阳的光辉,也许是波光粼粼的河水成就了翠鸟的灿烂。
冬天确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寒冷。四季都泛青的垂柳披着一身温暖,在河水荡起微波的时候,舞起了它的纤纤素手。冬天的垂柳也如此开放。芭茅比夏天还要繁荣,随着垂柳的浪漫摇曳出一片褐色。原来芭茅的成熟季节是在冬天。绿道旁有花树,我同样不知道名字,只是觉得花儿很好看,红色的,盛开的。红色的花根处有一圈嫩白色,我想,红色的花是嫩白色蓬勃出来的,而嫩白色则是花枝和泥土孕育的。
翠鸟是在我走下河堤、踏上绿道的刹那,飞过来歇在了我的脚边。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歇在我的脚边,反正它已经歇在了我的脚边。它的身上,有蓝的颜色,有绿的颜色,在蓝和绿之间,还有一绺金黄色。我们相望久了,似乎有些累了。翠鸟向前面跳了一下,我笑了一下,我们开始散步了。
翠鸟并不怕我。也许它不怕任何人,也许这里的环境让它乐意与人为伍,也许它想成为我心中的精灵。我对翠鸟说:“冬天来了,你好吗?你不怕冷吗?”翠鸟闪了一下翅膀,算是回答。我向前面缓步走去,翠鸟从我身后飞起来,从我的头上掠过,还鸣叫了一声。翠鸟的叫声我形容不准确,那叫声钻进我的耳朵里,听起来像河里碧绿的水,像飘逸的柳,像盛开的花,像成熟的芭茅。现在我可以确定,翠鸟先前从河面飞来,它身后剪影出闪烁的阳光,是翠鸟自己的。翠鸟刚才那一飞,我相信我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翠鸟看见我走得慢,又返飞到我的脚边。我已经站住脚,喘气,我有一些累了。我伸出手去,翠鸟居然跳到了我的手心来。我看了翠鸟的眼睛,睫毛不长,单眼皮,黑眼珠转动的时候,闪着光。我读不懂翠鸟的语言。我皱了一下眉头。其实,翠鸟歇在我的手上,就是最好的语言。也许翠鸟需要向我解释什么,它斜了我一眼,又飞走了。
翠鸟没有飞去很远。翠鸟飞到我看得清楚的地方,潜到了河水里,半晌才露出头,河水荡起圈圈涟漪。翠鸟腾空扑腾了几下身子,又飞到岸边的花树上面去了,花树浅浅点了点头,翠鸟又飞到柳枝上去了。翠鸟最后飞到褐色的芭茅上,然后从这根芭茅秆跳到那根芭茅秆上。过了好久,翠鸟才又飞到我的脚边。
翠鸟望着我,似乎在说:“明天来吗?”我说:“不来。”翠鸟好像不太高兴,单眼皮皱成了双眼皮。我微笑了一下:“好。我明天来。我刚才哄你的。”翠鸟的黑眼珠又转动起来:“真的吗?”我说:“真的。不管天晴下雨,我都会来。”翠鸟飞走了,它身后的剪影依然拖着一串闪烁的阳光。
冬天确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寒冷。也许是冬天没有真正到来。不过,我对冬天已经有了深厚感情,今天以后的冬天,也许很寒冷,也许有暴风雪,但是冬天不过是孕育春天的密码而已。
望着晚霞,不知怎么的,我就相信了一件事,我相信我明天去到河堤下的绿道,那只翠鸟还会飞来歇在我的脚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