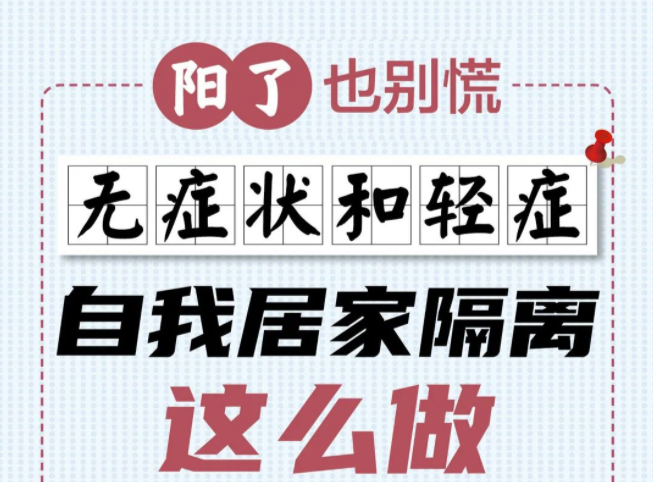□汤飞(绵阳)
奶奶在电话中高兴地说,她刚收了几分地的花生,约有一百来斤。这种透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消息让人倍感温暖。它们是熬过了长时高温、干旱的幸存者,据说一株藤上仅有寥寥几粒果实。
那片花生地位于家门口,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十年以前,各家的土地东一块西一块,上山乃至翻山实属寻常。平处、距家近的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农作物,花生等多偏居于山地,偶尔轮换,亦处于边边角角。后来,平地连成一片、集中划分,加上农夫渐老,花生才有机会提升自己的“番位”。不管被种在哪里,面积大小,贫瘠或肥沃,哪怕苗不过膝,花不如油菜花娇艳,果不成熟不外露,也坦然处之,从不争不抢不气馁,努力成长,回报人们的厚望。
花生家家皆种,普通却百搭。生熟无忌,刚摘的细嫩多汁,干透的别有滋味,蒸煮炒炸自可,咸甜辣均好。上得了宴席,做得了零嘴儿,一时饭菜未好,填肚子也行,还能与肉骨同炖、米饭同煮。即便跟另几位以“枣生桂子”的喜庆组合亮相,似乎也不出众:色彩不够鲜艳,形状不够圆滑。然而,平日里和嘴巴接触最多的,还是平平无奇的花生。
在我的住校生涯中,花生充当过主角。下饭菜需存放多日,此时,它的优势突显无遗。先在石臼里将花生米捣碎,我总是耐不得烦,捶几下便请奶奶检验,她看一眼,说“继续捣”。我无可奈何,只得接着使劲,直至它们通通化粒为渣,油脂让臼底变得光亮。然后,爷爷用菜油翻炒,待凉透再装入玻璃罐,随我返校。每顿饭搲两勺,下饭或拌饭,足以使人不馋肉味,还可用它跟别的室友交换,品尝隔碗之香。
在零花钱允许的情况下,我喜欢花一毛钱去小卖部买两颗花生糖,含在嘴里不忍咀嚼,用味蕾感受它慢慢融化的美妙,缓解刻苦之味。鱼皮花生、糖霜花生更是诱人垂涎的佳品。其实,花生还有更知名的粉丝——一向自律甚严的刘德华同样对它爱不释口。
有一年,花生喜获丰收,爷爷装了半袋去镇上油坊榨成油。带回来的除了壶中的油,另有袋中的油枯——形似树皮的花生渣。尽管可以食用,但又干又硬,再聪明的舌头也辨不出两者的关系。
离家多年,花生依旧是我与故乡的重要纽带之一。动身之前,行李包中常有其一席之地,点缀单调的日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和“身在福中不知福”同义,当穿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回望,才真切地明白牵挂亦是一种幸福。
记忆里总有一阵风,不时吹过家乡的花生地,绿油之苗起伏如波,却不会涌出四面的田埂。论默默无闻以蓄能,农家人犹如花生;论适应环境以竭能,花生好似农家人。彼此一道在同一块土地上顽强生长,改变着乡村的模样。丰收是一个结果,付出才是那个需要浇灌心血的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无论何时,一念及家园,脑海里自然浮现出即将丰收的花生地。抓住细藤用力一扯,一粒粒满身泥土的鲜活花生跃动着,急不可耐地诉说破土而出的欢喜……